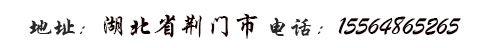入侵植物藿香蓟与常见伴生杂草的生态位特征
|
摘要 基于传统生态位理论的生物入侵机制假说都认为外来种和土著种生态位的差异是决定入侵成功与否和危害程度的关键。藿香蓟(AgeratumconyzoidesL.)是一种在我国南方快速蔓延的恶性入侵种。为了了解藿香蓟与其他杂草在群落中的生态关系,探究造成藿香蓟成功入侵的可能机制及危害,在浙西南的丽水市开展了杂草群落调查,计算了藿香蓟和16种常见本地杂草的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和种间相关系数,并对主要物种进行典范对应分析(CCA)排序。结果表明(1)藿香蓟与常见本地杂草间的生态位重叠度显著高于本地杂草间的生态位重叠度,这与藿香蓟具有最大的生态位宽度有关;(2)藿香蓟与常见本地杂草的Pianka生态位重叠指数介于0.04—0.之间,重叠度处于中下水平;(3)常见本地杂草对于藿香蓟的n-维超体积生态位重叠值显著高于藿香蓟对于常见本地杂草的n-维超体积生态位重叠值;(4)藿香蓟在CCA排序图上处于较中心的位置,说明其具有较高的中生性;不仅如此,外来杂草和本地杂草在排序图上充分混杂,说明外来种相对于本地种并无明显特征;(5)群落中大多数常见杂草间未出现显著种间负相关,仅7个种对显著正相关,大多数种对不相关。总的来说,丽水农村的杂草群落稳定较差,资源相对充足,种间生态位重叠较低,本地植物对于藿香蓟的竞争阻抗较小,加上藿香蓟本身较大的生态位宽度,导致了藿香蓟在本地区广泛而严重的入侵。 关键词 入侵植物;本地植物;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排序 引言生态位反映了物种在一定层次和范围内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及其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解释生物入侵的众多假说中,很多都明确或隐含地认为外来种和土著种生态位的差异是外来种能否成功入侵的关键。例如,空余生态位假说认为成功入侵的原因在于外来种恰好占据了生态系统中的空余生态位;干扰假说和资源机遇假说认为通过不同的机制产生了“生态位机会”,从而有利于外来种的入侵;物种多样性阻抗假说则默认了物种多样性高的群落中空余的生态位更少,因此更难以被入侵;而达尔文归化假说则认为和本土物种亲缘关系远的外来种更容易归化,因为它们和本土物种差异大,生态位重叠小,种间竞争弱。另一方面,生态位重叠是物种间利用性竞争排斥的必要条件。外来种和本地种的生态位关系不仅与外来种能否成功入侵有关,而且关系到外来种入侵后造成危害的严重程度。因此,在群落中研究外来种与本地种的生态位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外来种的入侵机制以及它们造成的危害具有重要意义。 藿香蓟(AgeratumconyzoidesL.)是菊科(Asteraceae)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热带美洲,于19世纪传入我国华南,现已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该种喜温暖、阳光充足的环境,对土壤要求不严,分枝力强。由于其具有较强的化感效应、光竞争能力、种子繁殖能力和表型可塑性,已对包括我国南方在内的旧大陆热带和亚热带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影响。在我国亚热带地区,藿香蓟常见于农村荒地、疏林、乡村路边、垃圾堆或溪边等地,常和其他外来入侵植物或本地杂草共生形成杂草群落。 (研究原因)为了了解藿香蓟与其他杂草在群落中的生态关系,探究造成藿香蓟成功入侵的可能机制及危害,为制定相应防治对策和措施提供决策依据,本研究在浙西南对杂草群落开展了广泛的调查,分析了藿香蓟和其他常见杂草的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情况。生物成功入侵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具有较高的生态位宽度。许微楠等人的实验研究表明,藿香蓟对不同的光照、土壤碳氮比和水分条件表现出较强的表型可塑性,其生态适应性很强。因此,本研究预测藿香蓟在群落中会有较宽的生态位。根据传统生态位理论的预期,受藿香蓟入侵的杂草群落应该很少出现与藿香蓟具有较高生态位重叠的本地物种。一方面,资源利用效率、对抗天敌取食和生长繁殖能力(即竞争能力)较强的本地种将阻止与它们有较高生态位重叠的外来种入侵;另一方面,藿香蓟实现入侵后,与藿香蓟有较高生态位重叠的竞争能力较弱的本地种将首先被藿香蓟挤出原生境。 1材料与方法1.1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的野外群落调查在浙江省西南部的丽水市莲都区(28°06′—28°44′N,°32′—°08′E;面积约.1k㎡)开展。莲都区处在括苍山、洞宫山、仙霞岭3山脉之间,地形属浙南中山区,以丘陵山地为主(面积占45.18%),间有小块河谷平原(面积占26.3%)。基岩主要为沉积岩、花岗岩和白垩纪凝灰岩,土壤类型主要是黄红壤、红壤和黄壤,农耕区以各种类型的水稻土为主。莲都区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降水量.5mm,年平均气温18.5℃,具有明显的山地立体气候特征。全区目前森林覆盖率约为79%,动植物资源丰富。 1.2群落调查 —年(每年的5—12月),在莲都区84个行政村的乡村路边、弃耕地、溪边、果园等处调查了个1m×1m的植物群落样方,其中81个样方被藿香蓟入侵,其余28个样方未被藿香蓟入侵。每村设置样方1-3个,同村的样方间距大于m。在野外收割每个样方内的所有植物的地上部分,带回实验室后将所有植物进行分类(按种)、称量其新鲜质量(鲜重)、计数并鉴定。 1.3土壤取样和理化性质分析 群落调查的同时,本研究现场调查了每个样方的土壤干湿度(分为5级)、坡度、坡向、海拔和受光率,并记录调查日期。受光率为样方正上方的光照强度和附近无任何遮阴处的光照强度的比值。在样方的4个顶点和中心处取10cm深的土壤,剔除石块和较大的植物残体后合并为该样方的土样。(五点取样)土壤样本带回实验室,自然风干、研磨过筛后分析土壤的PH值、全氮含量、水解氮含量、有效磷含量、有效钾含量和有机质含量。生境调查和土壤理化性质分析更多细节详见郑珊珊等人的论文。 1.4数据处理和分析 1.4.1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度 本研究分别用两种方法计测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以期更准确地了解丽水农村杂草群落的生态位特征。为了更简洁地呈现丽水农村杂草群落的生态位特征,本研究仅分析藿香蓟及其它在样方调查中出现25次以上的16个常见种[全为本地种。本研究共调查到种植物(含种下分类单位)]。17种常见杂草的基本信息见表1。 首先将1m×1m的样方作为一个综合资源位,以各物种在各资源位(样方)的地上鲜重作为多度指标来计算物种的生态位宽度和种间的生态位重叠度。生态位宽度反映物种或种群对环境适应的状况或对资源利用的程度。生态位宽度计测采用Levins公式中的Shannon-Weiner指数: 式中物种i的生态位宽度,=,即种i对第k个资源的利用占其对全部资源利用的比例,是第i个物种利用资源状态k的鲜重,是该种所有资源状态中的总鲜重,r为资源状态总数,即样方数。该指数的值域在0—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生态位越宽。 生态位重叠是2个或多个物种或种群在适应环境和利用资源的实际幅度或潜在能力方面所表现出的共同性或相似性。在传统的生态位计测方法中,我们选用对称α法,即Pianka指数计算常见种间之间的生态位重叠。 式中为物种i和物种j的重叠指数;和分别为种i和种j在资源k上的利用比例,计算时用种i和种j的鲜重占样方k的植物总鲜重的比例来表示。该指数的值域也在0—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生态位重叠度越高,便于对不同种群的生态位重叠进行客观比较。 上述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计测公式虽然都有明确的几何学解释,生物意义明确,并且充分利用了物种在不同综合资源位上的多度信息,但是都没有考虑到资源的可利用性。为考虑资源含量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本研究调查的生境数据(含调查日期,即生长季节),我们使用基于概率的方法来计测杂草群落常见种的n-维超体积生态位重叠。生态位重叠度()被定义为在物种B的n-维超体积生态位范围内物种A的个体出现的概率。 物种的生态位范围()被定义为一个特定的n维空间,在此空间内找到满足物种生存所需条件的概率为α(如95%),即 上述两式中n为生态位维数(或生态因子数),X为出现某物种的生境中各生境因子(n维)的观测值,服从均值为μ,方差为Σ的多元正态分布,C为(X∈)=95%时的常数。在具体应用中,由于均值μ和方差Σ都是未知的,因此需要基于调查数据进行参数估计。Swanson等人建议利用贝叶斯法来进行参数估计并计算估计值的不确定性。考虑到季节变化具有周期性,本研究以2月3日(立春)作为一年中的首日,各调查日期先转化为相应日序(值域为1—),再将日序乘以2π/后进行余弦转换。坡向也是环形变量,原始数据同样进行了余弦转换。 Shannon-Weiner生态位宽度指数和Pianka生态位重叠度指数的计算使用R语言的spaa软件包。基于概率方法的n维超体积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计算采用R语言的nicheROVER软件包。 1.4.2典范对应分析 近年来,多元统计在生态位分析中不断得到应用。该方法可以把多个与种分离高度相关的生态参数进行合并或剔除,使维数降低且互相独立,能将物种间的生态关系更直观的呈现出来。如郭水良和曹同应用典范对应分析(CCA)探讨了长白山金发藓科植物的生态位分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除了直接计测常见种的生态位宽度和重叠,本研究也利用典范对应分析研究杂草群落中主要物种与藿香蓟的生态关系。本研究用R语言软件包vegan进行典范对应分析。 1.4.3种间相关分析 为了回答与藿香蓟具有较高生态位重叠的本地物种是否较少出现在受藿香蓟入侵且其优势度较高的杂草群落的问题,本研究分析了藿香蓟及16个常见本地种的种间关系,并进一步分析种间关系的亲密程度和种间生态位重叠程度的关系。种间相关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来衡量,并用t-检验来检测种间相关的显著程度。 式中代表种i和j之间的相关系数,r为样方数,和分别是种i和j在样方k中的鲜重值,和分别是种i和j在所有样方中鲜重的平均。 2结果与分析2.1常见杂草种群的生态位宽度 对丽水农村杂草群落中17种常见杂草的生态位宽度分析表明,藿香蓟的生态位宽度最宽(0.),其他杂草的生态位宽度适中,Shannon?Weiner生态位宽度指数均介于0.40—0.65之间(表2)。除藿香蓟以外,生态位宽度相对较宽的还有升马唐(Digitariaciliaris,0.64)、碎米莎草(Cyperusiria,0.60)和铁苋菜(Acalyphaaustralis,0.59)。生态位宽度最小的是细风轮(Clinopodiumgracile),Shannon?Weiner生态位宽度指数为0.41。 2.2常见杂草种群的生态位重叠 以Pianka指数计测的生态位重叠度分析表明,常见杂草间的生态位重叠度在0.5以上的种对仅2对,分别为狗尾草(Setariaviridis)和牛筋(Eleusineindica,0.54)、酢浆草(Oxaliscorniculata)和碎米莎草(0.52)。生态位重叠度在0.3-0.5之间的种对有升马唐和牛筋(0.41)、匍茎通泉草(Mazusmiquelii)和短叶水蜈蚣(Kyllingabrevifolia,0.36)。其余种对的生态位重叠全在0.3以下(表2)。外来杂草藿香蓟与其他常见本地杂草的生态位重叠度介于0.04—0.之间,显著高于本地杂草之间的生态位重叠(P=0.04)。直线相关分析表明,某种杂草与其他杂草的平均Pianka生态位重叠值与其Shannon-Weiner生态位宽度指数呈显著正相关(r=0.72,P<0.)。 n-维超体积生态位重叠分析表明不同种对之间生态位重叠程度差异较大,值介于0.00—0.94之间。短叶水蜈蚣对于藿香蓟的n-维超体积生态位重叠值最高,达到了0.94;另外无辣蓼(Polygonumpubescens)、叶下珠(Phyllanthusurinaria)、铁苋菜和升马唐对于藿香蓟的n-维超体积生态位重叠值都很高,分别为0.86、0.83、0.82和0.80。这说明这些物种的个体生长所需的环境大部分与藿香蓟的生态位空间重叠。同时,各常见杂草对于细风轮、无辣蓼和龙葵(Solanumnigrum)的n-维超体积生态位重叠值几乎为0(表3)。进一步分析表明本地杂草重叠于藿香蓟的程度(表3第1列)显著高于藿香蓟重叠于本地杂草(表3第1行,成对t检验P<0.)以及本地杂草间的相互重叠(成组t检验P<0.)。直线相关分析表明,其他物种(作为物种A)对于某物种(作为物种B)的平均重叠度与该物种(物种B)自身的Shannon-Weiner生态位宽度呈显著正相关(r=0.84,P<0.);而某物种(作为物种A)对于其他物种(作为物种B)的平均重叠度与该物种(物种A)自身的Shannon-Weiner生态位宽度无关(r=-0.27,P=0.28)。直线回归分析表明每个种对的n-维超体积生态位重叠的均值与Pianka生态位重叠指数呈显著正相关(β=0.58,P<0.),但解释度仅0.23。这说明上述两种生态位重叠的计测方法反映的物种间生态位重叠具有一致的变化趋势,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3典范对应分析 对83种出现频度较高(至少在5个样方中出现)的植物进行典范对应分析,从前4个排序轴来看,外来杂草和本地杂草充分混杂,并没有出现外来杂草或本地杂草各自聚成种团的现象(图1)。这说明外来杂草和本地杂草具有一定的生态相似度。相对于本地杂草,外来杂草并无明显的生态特化。特别是本研究重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xiazhua.com/yxzgyzz/10273.html
- 上一篇文章: 女造景师最喜欢的水草,没有之一
- 下一篇文章: 纯中药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