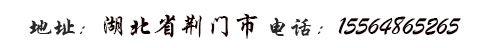长篇连载曾经沧海,第十一章
|
《曾经沧海》 第十一章添田置地 程老先生不仅坐诊给人看病,还在危难时刻出手相济,牛大脚对于程老先生自是感恩戴德,但因欠着程老先生店里的钱又羞于开口。这一次他来到福兴堂药店,将刚从怀里掏出的药方子,又生生给掖了回去,这一幕正好被程老先生看个真切。程老先生赶忙从诊室里出来,一面要他将药方取出交予店里的伙计配药,一面扶着步履蹒跚的牛大脚留他吃饭。牛大脚死活不同意,但又拗不过程老先生的热情,吃罢晚饭,牛大脚再次走进梧桐镇的福兴堂药店,脸上的面孔和他的心境正好相反。他心里燃烧着炽烈的痛苦火焰,脸面上摆着却是可怜兮兮的无奈,那种憔悴又羞愧的神色,令人望之顿生许多怜悯。 “老先生啊,我是个不肖子孙,祖上留给我手头的那点田产,今天要在我的手上败光。”他带着一副哭腔欲给老先生下跪,但被程老先生一把拉住,接着他又声泪俱下向程老先生述说,最近经历家业凋零家道不济的霉运,那些无法启齿又人人皆知的祸事,哀叹自己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穷途末路,哀叹自己命里注定祖先家业要在他的手里落败。他还哀叹自己命运不济,甚至已到不可扭转的地步以博得他的同情。 程老先生虽然百般安慰,但他还想以下跪的方式恳求:“老先生,可千万给我想条出路啊!我走到这一步路已走绝了,下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也得往下跳,昨夜思来想去别无他法,只好卖掉老租宗留的那块心头肉。” 程老先生懂他心头肉的意思,指的是靠近繁花里大鲤池岸那几亩田地。他把繁花里挨家挨户捋了一个遍,有能力买走这几亩田地的除了夏老爷子,再也数不出第二家来。他知道程老先生与夏老爷子两人交好,所以这事只能反过来求程老先生。 “变卖祖业是忤逆子孙啊!将来在繁花里甚至梧桐镇都落下败家子的名声。”牛大脚说到这里时已经潸然泪下。他恳求程老先生看在自己可怜的份上,能出面说服夏家,居中介绍。 这一回,轮到程老先生冷静地听他把话说完。之后,他冷冷地问道:“你再想想别的法子,不卖地行不行?”程老先生是欲擒故纵,他不能顺藤摸瓜,必须得反着自己的思维去问他。他自己虽不是买主,也要躲开乘人之危的嫌疑,否则顺带将自己安上与人合谋的恶名,这中间人一定要做得让牛大脚心服口服。 “老先生啊,除了卖地没其他办法了,除此之外值钱的就剩下一头黄牛,再说我的这双脚卖了牲畜怎么种地?我翻来覆去想过无数次了,只有卖地一条路可循。”程老先生凝重的面孔似乎被他说动:“药钱不够可以从我这里再支,地是决不能卖。你卖两亩地容易,再置二亩地就难了。眼看着你卖地还要我做中间人,你说说怎么个卖法?” 程老先生出于对夏老爷子救命之恩的回报,在这件事情上尽心尽力,两边都是乡里乡亲的,一个深陷水深火热要卖地赎命,一个家境殷实想要买田置地,无非是各取所需。程老先生在梧桐镇行医多年,平日里给人号脉问诊,像牛大脚这号的病人见过不少,那些被命运击倒的人,宁可拉棍子出门要饭,也不会松口卖掉自己的命根子。偶尔有忍痛割爱卖地的大都是出卖贫瘠的旱地,实在有揭不开锅的咬咬牙卖掉水田,也不过是缺嘴短腿的废地,这些地一般种田人都嫌弃它看不上眼。这一回倒好,遇上个牛大脚七跪八拜的求着自己,可见真到了走投无路的份上。 他哀叹他的不幸,凭他自己的能力仅能接济他于一时,救得了他的病,却救不了他的命,如何想出个两全其美能让双方都能满意的办法,也不枉他一世英名。牛大脚见程老先生半晌没有响动,又怯怯地问了一句:“老先生是不是不愿意?那我也不能勉强你。” 程老先生从犹豫中回过神来,他将脑袋往上一抬说:“大兄弟啊,这买卖田地非同儿戏,你再给我说说这家里五亩零三分的水田全部都卖掉,还是卖掉一部分?”牛大脚话里听出程老先生的意思,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一半,连忙说:“全卖,我全部卖掉。反正我这个样子也无法再种地了。” “慢!”程老先生将一只手举到半空,打断了牛大脚的说话,“依我看你将这五亩三分的田卖掉三亩,剩下的两亩零三分你给自己留着。” “老先生开什么玩笑呢?”牛大脚听程老先生这话有点摸不着头脑:“难道老先生怀疑我不是诚心诚意的卖地?在繁华里一带,小家小户的谁能一次性买走我的五亩地?我心里明镜似的,除了夏老爷子能出这个钱,没有别家。” 程老先生这下大笑起来,他拍了拍牛大脚的肩膀说:“大兄弟啊,我这可是为了你好。你看你这样子还能种地吗?你心里也甭含糊了,其实夏老爷子买下这地是给你解危救急哩!你就不要再顾虑什么了。我的意思剩下的两亩零三分就交托给夏老爷子照管,你就按年收取这部分的租金或谷物,你一年到头的衣食倒也无忧了。” 牛大脚愣了一下:“我这不是成了地主吗?”等他转弯过来,又感天动地的给程老先生下跪:“老先生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老先生给我想得这么周全,我牛大脚来生来世给您做牛做马都愿意。” 程老先生急忙扶他起来,“大兄弟,使不得,使不得啊。”牛大脚还有疑虑,便问道:“老先生,你说这样子夏老爷子会同意吗?”程老先生捻了捻他的山羊胡子,照着一脸狐疑的牛大脚说道:“大兄弟既是这样说,那就照我的意思办算啦!这事嘛,我会跟老爷子去交涉的,他多少会给我面子,就当他也帮你一把吧!”至此,牛大脚心里完全放心下来,从初听到这个喜讯时的惊喜,变成真实可靠的踏实,他的心情随之平缓下来。 经过程老先生这一番用心,既排除了乘人危难夺人家产的坏名,又坐实了牛大脚卖田而不会中途变卦,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他为自己下的这着妙棋感到庆幸。送走了牛大脚,他就亲自将这喜讯告诉夏老爷子,夏老爷子听闻之后心里自然欣喜,病也好了一半,但他仍然装出一副不为所动的神色:“人家牛大脚遭受不幸,他若真心卖田,我咋能不买呢?我这不是见死不救吗?” 程老先生笑着说:“我仅能开开方、号号脉,人家都说治病救人,幸亏那大脚命好遇上老爷子,还是老爷子功德无量。”夏老爷子故意正色道:“老先生这样说不是存心折我的寿吗?我怎么能跟您这个神仙相提并论呢?” 接着两人相视,一阵哈哈大笑:“来来,要不要抽一口?”夏老爷子摆弄着手里的旱烟筒子:“我已经好几天没动过这家伙了,今天高兴非得过把瘾不可。”程老先生赶紧摆手:“行啊你,一盅烟臼就把我收买了,我们还是说正经事要紧。” 当下两人就买卖的细节问题做了简要的商议,包括定下写契的日期,一亩按市价折合多少银两或者稻谷,这样子程老先生可以制定一个合理的价位,最后还将牛大脚留下的两亩田产交给夏老爷子托管的事,也顺便作为附加件条件交代一番。夏老爷子的意思那三分零头的地也卖给他,就整出两亩的地供他照管,一是方便计算进出谷租银两,二是那三亩三的地是一个整块再另外划分就不便管理,希望程老先生再带话给牛大脚考虑。 听了程老先生的传话,牛大脚没有不同意的道理,感激都来不及,二话没说就接受了。眨眼间过了正月,夏老爷子指派家里的长工显良,到梧桐镇上的“乌皮饭馆”订下了一桌酒席。二月初十是约定的写契日期,程老先生在方桌的上首位坐定,右边坐着牛大脚和他的老娘舅,左边则坐着夏老爷子和允钰,程老爷子的对面坐着从店里请来代写文书的账房先生。 夏老爷子叫乌皮掌柜上了一壶上好的烧酒,乡里的规矩凡买卖田地房屋都要由买主做东请中间人一桌酒菜,买卖双方请来当地有名望的人做中人,在这宴席期间将买卖的细节敲定。俗话说“万里江山一点墨”,双方在这期间达成协议,一旦形成截断买卖的契约,卖方的财产就归买方永世管业,无论生死都不得反悔,这就是乡间所说的“卖断死契”。 程老先生做事向来精细明察,没有多余的客套寒暄,刚待卖卖双方落座,率先举起酒盅与几位一干而净。酒碰三次,言归正传,程老先生就直奔主题:“诸位,承蒙两位家长看得起老朽,今天也不啰嗦了,还有什么话想说的就赶紧说,凡今天过后就没有再说的道理。”大家也没多话,双方的心里都翻滚着波涛,至少于牛得草而言经历这种场面有些落寞。 房间里静得只听见噼里啪啦拨动看算盘珠子的声音,程老先生连拨了三遍,他首先声明从大清流传下来的一项规矩,即按照一亩田地大体可以折合几千文铜钿计算。这样就推算出夏老爷子应该净给牛得草的银两,如果按市价折合成粮食或银大洋应该是多少石多少圆。在众目睽睽之下,算盘珠子的声响突然戛然而止,程老先生就歪过头对老账房先生说:“我的帐已经算好了,现在该轮到你忙活了。” 账房先生接过长工显良送来的砚台,开始研墨。他被请来的职责非常明确,那就是双方把话说明以后,按照口头内容写买卖土地的契约。账房先生嘴里念念有词,一阵摇头晃脑便将草拟的合约内容口述一遍,双方均点头表示没有异议,然后他略加斟酌,蘸笔开始在宣纸上一阵行云流水。少顷,又信手举笔在半空挥舞涂抹几下,只听得刷刷刷毛笔行走在纸上的声音,落笔犹如行云流水。账房先生不愧喝墨水出身,不消一顿饭功夫,一幅游龙飞凤般的墨笔字即跃然纸上: 立截断卖约人牛得草因病无钱使用,今将祖遗民田,位于大鲤池南北通坂田地一坵,共计土地三亩三分二厘五毛,同中人程老先生说合,情愿卖与繁花里夏顺兴名下为业。言明每亩卖京钱二十千零三百三十文,共卖京钱六十九千零二十文,折合大洋叁佰玖拾陆圆整,卖日交足。该坵坐落圣屿乡土名大鲤池岸,界限东至:大鲤池;西至:张至立和夏顺兴田路;南至:夏先文田沟;北至:何小奶水坑。交限四至分明。 又牛得草管下另一坵田,坐落五亩池与墩池岸交界处,田坂合计两亩整,因无力耕种,今交予夏顺兴管业,夏顺兴每年须向牛得草交田租折合谷物壹拾贰石。卖出之田产自交割之日起,再与牛得草无涉,不得取赎,生死无悔。恐口说无凭,立此绝卖约存证。本契一式两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 附开 长科七十岔零八寸五卜,北中南横十乙岔零五寸,大鲤池岸坟地内除二厘五毛。 立卖契人:牛得草(画押指印);买受人:夏顺兴(章);作中人:程瑞凤(章);代笔人:窦世仁押。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阴历二月初十日。 不知从哪个朝代起,繁花里的先人故后,按照祖上流传下来的规矩,须在自家田头停柩三年才能下葬,牛得草家也不例外,故这块地理应从地契里面剔除。账房先生写好契约,程老先生先接到手念了一遍,又交给买卖双方的主家都看了一遍。程老先生将笔交给双方签名画押,牛得草不太识字由账房先生先写他再依样画葫芦,夏老爷子一方由允钰划拉一阵代签上名字,程老先生最后在中人款格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一切手续停当之后由账房先生签名落据。程老先生先生取来印泥盒子,四个人先后用食指蘸了红色印泥,然後一齐往契约上摁下去。最后程老先生往每人的酒盅里再斟上酒,大家一仰脖子饮了,这宗买卖仪式就算成了。夏老爷子长舒了一口气,感觉他苦心经营的家业又厚了一份,其实他的心里也是一片翻滚的波澜,那块渴望已久的田地终于属於他了。 夏老爷子梦里的场景终于变成现实,许多次他梦到自己正在牛得草家的这几亩良田里种地,他指挥着显良和其它几个帮工,他们四五个人正抬着一架长节蜈蚣似的水车,费力地将它浸入大鲤池的池水中。他又央了几双人手,他让他们日以继夜地趴在水车上车水,他们首先将大鲤池的池水翻灌到这几亩干裂的土地中,将原来因干旱而板结的田坂,通过车上来的水翻耕,改造成可以种植水稻的水田。 大鲤池岸最大的田坂不过三亩三,也就是牛得草家的这块田地,夏老爷子的梦想就是通过将它改造成水田以后,春天的时候插上秧苗,到了夏天就可以收成一季的稻谷,稻谷收割以后即再翻耕插上晚稻,等到秋天的时候又是一季的稻谷收成。单单这样还是远远不够,晚稻收割以后即将立冬,这时候得抓紧时间播上小麦,收了早稻种晚稻,种了晚稻播小麦,到了来年春天小麦收割以后,又可将它翻耕插上早稻的秧苗了。别的地一年最多只能两季,这里的地因为紧靠大鲤池这口巨大的池塘,就是旱季也能保种保收,一年种个三季根本不是问题。 这真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像聚宝盆一样源源不断地向他输送粮食,这样的田地买得太值了,越多越好,他在梦里都冲着自己笑了。夏老爷子的心里抑制不住的激动,开春也没有什么农事,他却急不可耐地规划起这三亩土地的蓝图: 第一步是划界。按照契约上双方口头达成的协定,牛得草留下的那一亩春小麦,折合成两担谷物后归夏老爷子,这样子就不用再去易地播种庄稼了。天色微明,夏老爷子父子俩就扛着锄头去了这坵新买来三亩三的田里,在这块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挖掉牛得草的界址,再重新标记属于自己的界址,这样重要的事情,允钰当然也不能落后。以往在繁花里发生过许多地界田梁上的吵骂和斗殴,将这些地界的权限明晰,一方面起着示范效应,另一方面起着楷模作用。允钰对准一块黑黝黝的顽石一锄头下去的时候,就听到一声刺耳的声响和铁石撞击发出的火花,这些湿漉漉泛着青光的花岗石被一个个挖了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勒有夏家铭文的青白色楔形条石,它们像星星一样点缀在细雨微醺的田野里。 第二步是种树。为了将这些田格之间加上一道防护林,夏老爷子将朝北的一段大鲤池岸植上水杉、乌桕、苦楝树等命贱易活的树苗,它们一来可以挡风,二来可以在盛夏来临时为劳作的人们提供纳凉遮荫,第三可以用来巩固堤岸防止水土流失。在树种的选择上也颇费心思,江南夏热冬寒,栽植的树木要符合夏天浓荫匝地,冬天阳光普照的基本原则。即既不能影响庄稼光照,又能为庄稼提供挡风防冻,按照这个原则,那些冬天的落叶乔木就成为首选;开春正是植树的好时机,老爷子可不想错失这个良机。 第三步是平田。沿着夏老爷子新埋下的界石,从南至北有一条永久的神圣无比的田梁,在庄稼人看来它们就相当于秋毫无犯的国界。牛得草的这坵田在外,夏老爷子的一亩三分田在内,但历史上在这条结埂的田路上长满胡葱、叶下珠、车前草、马鞭草、旱莲草、菅草、三棱草等杂草。田梁两边土地的主人都不容它们长到自家的田里,尤其有一种名叫“小飞蓬”的野草不容易被铲除,几代人以来它们就一直像今天这样生长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成为一道庄稼人的硬伤。夏家父子决定推倒这垄不可逾越的藩篱,这个想法一旦付诸实行,他们就已经动手刨挖这道田梁。从里面挖出的石块用以填路,从里面除出的杂草和泥块准备暴晒一周以后点火化成灰堆(草木灰),这条延续坚守着几代人生命的田梁,在沈海沈彪他们齐心合力帮助下,只需一天就可以物尽其用。它们在夏家父子的镢头铁锹下正一尺一尺地消失,到晌午后再让显良套上水牛用犁铧耕过,这条田梁就荡然无存了。夏老爷子让自家原有的一亩三分地,和向牛得草家新买的三亩地完全和谐地归并成一块,然后按照种植作物的功能,再重新划分新的田块。 第四步就是增肥。按照夏老爷子原来的设想,就是夜以继日的将大鲤池的池水抽干,然后取出池底的淤泥,将这些富含有机质黑油油的烂污泥输送到田里作为肥料,为刚买的牛得草家的三亩地增肥,增肥的目的就是改善土壤结构,将贫瘠的土质改良成适合水稻生长的良田。但是这项使用人力水车将池水车干的工程太过巨大,经过一番思量决定租用一条太平人的“捻泥船”,具体做法是与船主谈好租金,将由太平泽库[注20]出发的船只,经由南官河撑至梧桐镇水埠,由允钰出面雇30名青壮年,合力将船从河里翻上岸,每边由身材从高至矮排列10人,另外10人每边手拿毛竹与木头制的短驻(俚语,木棍的意思),作为乏力者的替补,一支浩浩荡荡的人工长龙,一路哼哧哼哧喊着号子,将木船像蚂蚁搬家般运至大鲤池里,然后开始捻泥。干捻泥师傅活计的也为太平向来的人,都是祖传下来的手艺,捻泥船每边站立一人,由一个底下装有畚箕似的长竹竿从远侧往人的近侧兜泥,兜泥时两人分工明确,一人把兜,一人负责稳住船的重心,兜满一船舱后再用戽斗将池泥戽往岸上,过半月余春耕后将泥块切割分往每个田坵里,混合事先化好的草木灰,和猪栏粪牛栏粪一起作为基肥。望着这个劳动场面,这个时候,夏老爷子的眼前仿佛出现一垄又一垄绿油油的稻苗,他的脸上映上了满足的微笑。 第五步兴水利。夏老爷子痛感祖辈以来种田靠天的困惑,为了保住一年以来辛苦的劳动果实,不致于因气候突变造成的灾害重演,防患未然,旱涝保收,所以他将这个田块规划了纵横的沟渠,使他们兼具灌溉和排水的功能。另外,他认为经营好大鲤池这口大池,是农作物丰收的保障。大鲤池名为池塘,实则是一口二三十亩见方的小型湖泊,因此由他发起召集池边有田的各户,在池的南北段各开了一条很深的沟渠,沟口各修水闸,用以调蓄池水容量。池里水生的植物养上菱藕,池边则种上茭白;为了维持平衡,光养这些还不行,池里还要养鱼,鱼种就近选择从鉴洋湖买来白鲢、胖头、鲤鱼的鱼秧放养。秋有菱藕飘香,年到湖里有鱼,这样子大鲤池也就名副其实了,这“年年有余”的年景经过这样一番改造就轻松实现了。 等夏老爷子做完这些,半年的时光忽地过去了,他手拿一杆旱烟立在大鲤池岸打眼眯看。眼瞅着那一池秋水,心里已有一架运转不歇的木耳水车,那木头旋转摩擦的声响,仿佛在他心里嘎吱嘎吱唱着一支动听的田园牧歌。终于可以拿出一点说道的东西面见先祖,他为自己的这些成绩感到陶醉。 (未完待续) -THEEND- tzchensha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xiazhua.com/yxzzpjs/5260.html
- 上一篇文章: 中草药大全gtgt肾炎用药篇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